
撰文丨鹽魚
排版丨馬馬子
?今夜,一起來“彈性”嗎?
“蔚藍的黃昏籠罩著全場,一只Saxophone正伸長了脖子,張著大嘴,嗚嗚地沖著他們嚷,當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頭發和男子的臉。男子襯衫的白領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著自家兒的神經。”
上面這段文字是穆時英在小說《上海的狐步舞》中對民國時期的上海舞廳所做的描述。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摩登文化”的風潮下,跑馬廳、跑狗場、回力球、咖啡館、電影院等新型娛樂方式逐漸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交誼舞廳就是在這時步入人們視野。交際舞又稱“舞廳舞”,是一種受西方喜愛的社會交誼手段,男男女女在昏暗的燈光、嘈雜的人聲、富有節奏感的樂曲和肢體接觸形成的迷幻氛圍中拉近了與陌生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從一言不發到低吟淺笑,腳步交錯、回旋不停,共度一段美好休閑的時光。

交誼舞又叫國標舞,包括華爾茲、迪斯科、探戈、恰恰、倫巴、布魯斯和吉特巴(水兵舞)幾種。傳入中國后,通俗叫法是依據節奏將布魯斯叫做“慢四”,吉特巴叫做“快四”,華爾茲有“快三”“中三”“慢三”幾種,還出現了“平四”這種國內獨創的形式。慢四節奏平滑、抒情浪漫,音樂和舞步間充滿“憂愁”色彩;快四熱情奔放、慷慨激昂,富有朝氣,最早是美國軍艦上的水兵跳的一種舞蹈;華爾茲優雅抒情,回旋擺蕩,起伏連綿,被列為國標舞第一舞種……“無論是在舞廳娛樂、消遣,還是在競技場上爭奇斗艷,交誼舞都以其特有的準確、飄逸、自然的舞姿,表現出一種莊重典雅、細膩嚴謹的風格。”
交誼舞傳入中國后,以上海為首,逐漸掀起一股跳舞的風潮。那時人們將“dancing”翻譯為“彈性”,將舞女(專業的陪舞女郎)稱為“彈性女郎”,就連著名的上海百樂門舞廳都采用了框架結構的、汽車彈簧支撐的彈簧地板,當眾人一起起舞時地板振動傾斜,助長迷幻興奮的氛圍。人們晝夜不息地跳舞,舞場也開始二十四小時營業,早場、午場、晚場不夠,還要增設茶場(下午四點)和通宵場,只有霓虹燈光不停歇地流轉,樂隊永遠奏響樂章,才能滿足人們剛剛掙脫傳統束縛、亟待抒發的沉積已久的欲望。
短暫的風華過后,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的營業性舞廳基本關停,交誼舞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蘇聯傳來的交誼舞和集體舞。直至80年代改革開放,舞蹈的熱潮隨著卡拉OK、健身房、臺球室、電子游戲廳等新一輪新興娛樂方式的到來重新席卷年輕人的生活。人人都在跳舞,不會跳交誼舞的年輕人被譏諷為“土老帽”,跳的好的更是備受追捧,成為舞場明星。除了大大小小的營業性舞廳如雨后春筍般冒出,更出現了專業的交誼舞培訓班。五十年前《申報》所記載的景象重新出現在繁華的街口:“在舞市的特區虹口這個神秘的地帶上,一到了整個都市歸于平靜的時候,它們(舞廳)卻正在開始他們神秘的工作。把許許多多彈性的善男信女,軟禁在它們那黯淡的陣圈之中,一直到日出!”下了班去舞廳“瘋上一瘋”,伴隨著“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閃爍/彷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顆”的歌聲,在華燈初上光影斑駁的舞池里與男伴或女伴轉上幾圈,成為了我們父輩那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回憶。
這也是今天,我們走進北京三環內一家交誼舞廳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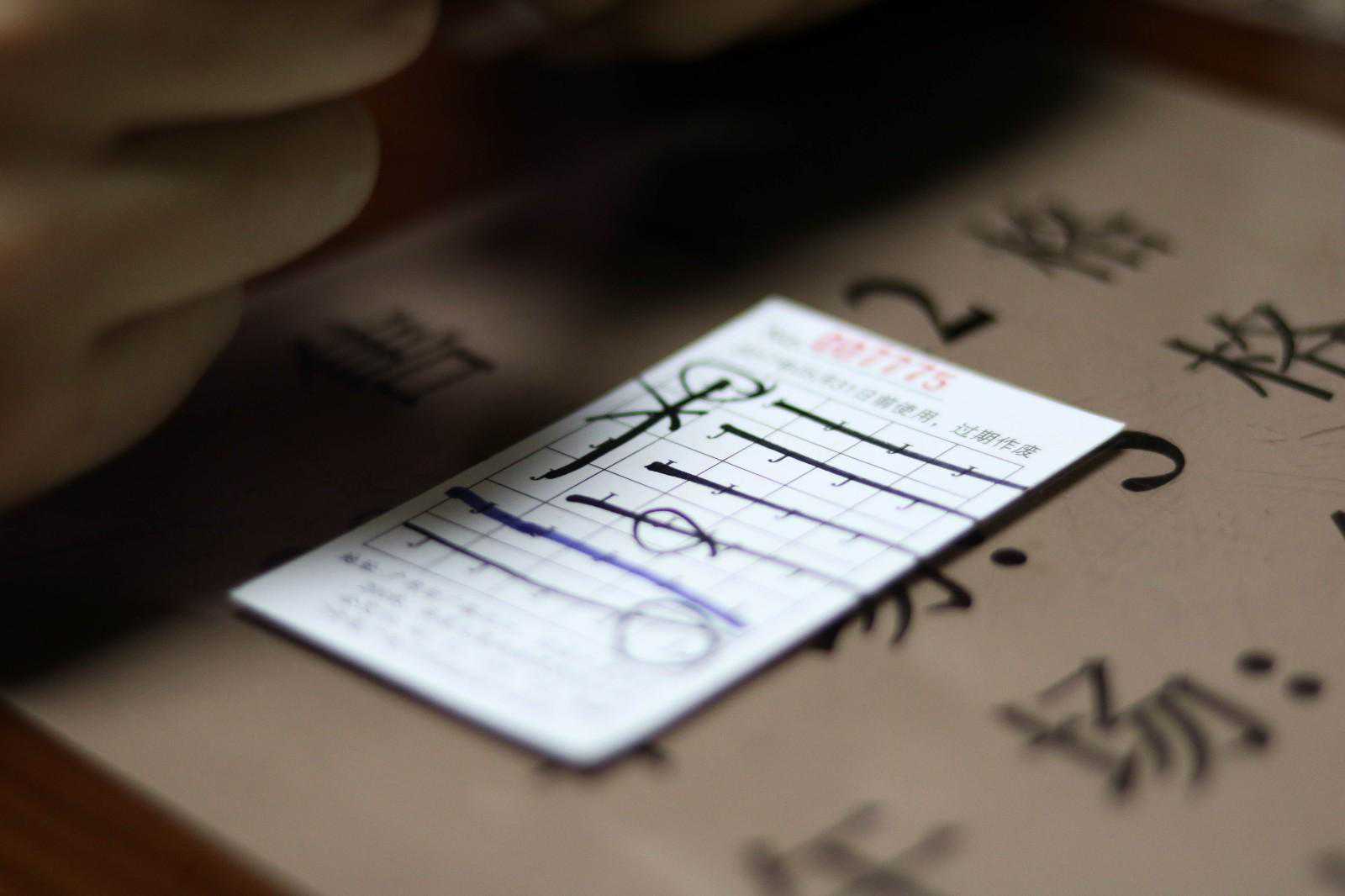
?風華與流變,一家舞廳的現實
位于一個小胡同里的這家舞廳,是現今北京三環內罕有的一家營業性舞廳,從07年開始營業,迄今為止不過十年,然而它卻有悠久的歷史。
“這家開了三十幾年,然后才搬到這的。”一位來跳舞的大爺說。
舞廳誕生于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有過許多前身,如今深藏在胡同里的這個已主要是老年健身活動中心,不過幾十米遠處就有兩家養老院。
負責人告訴我們,這里每天有三場舞,早場上午八點半開始十一點半結束,下午場兩點開始,晚場七點半至十點。
舞廳很低調,藏在兩根電線桿中間,不掛招牌。沒到點的時候也開著門,只是沒有燈光,舞場遙遙隱沒在黑黢黢的走廊背后。走過貼在玄關處的全身鏡,幾塊被擦得锃亮的瓷磚,穿過幾張小飯館里常見的飯桌,往右看,五、六百平的舞廳就在眼前。

門口的收營臺。過去被稱作“望鄉臺”,供賣舞票、收茶資和監視舞女與舞客行動所用。大家叫它“望鄉臺”,其意為地獄中的靈魂在探望親人,藐視柜臺后的老板爪牙。
入場跳舞需要買票,可以辦卡。許多常客都會辦一張跳舞卡,這樣更劃算一些。收營臺除了負責收銀,也會賣舞蹈服、舞鞋、飲料,不過來這里跳舞的人早已在家準備齊全,所以各式男女舞鞋在玻璃柜里堆成了一座小山。


跳舞卡
七點半,晚場開始。打頭陣的是一位燙了頭發,穿著橘色長袖毛衣、黑色短裙和長筒靴的女士。隨之,人們陸陸續續到來,半小時后原本空曠的舞廳就已人頭攢動。來跳舞的多是中年人,四五十上下。負責人說早場主要是老年人,午場是中老年,晚上中年人多一些。“大家下了班吃了飯就來這里跳舞,有些人家里有小孩兒要照顧,所以晚上不能來。”
幽暗的藍色燈光中,人們的面容隱藏在朦朧的光暈之下,舞廳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為來這里跳舞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彼此相邀、熟識的絕佳機會。最明亮的地方是位于中央的舞臺,那里是現場樂隊演出的地方。舞臺上方的裝飾燈安了一圈,形成流蘇一串串掛下來,頗有些“火樹銀花”的意思。現場樂隊是老板請過來的,都是民間的業余愛好者,一名架子鼓,一名小號,一名薩卡斯和一名合成器,付些出場費,四個人便為舞者們奉上絕妙的氣氛“催熟劑”——舞曲。
跳舞的人形形色色,齊聚一堂。一部分人穿著運動服、休閑裝輕松上陣;一部分人則鄭重其事,男士穿著白襯衫西裝褲黑皮鞋,女士則化上妝,深色眼影長睫毛,紅艷艷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寶藍色大擺裙在搖曳的步態中輕輕飄蕩。挺直的脊背與標準的舞姿,使得每一場舞極具儀式感。
在成雙成對旋轉的人之外,不免有落單的。比較害羞的就坐在長椅上,等待他人相邀;也有一二沉迷跳舞的,便獨自在歡快的音樂里扭動起來,無論是成對的還是獨身的,都沒有人向他人投去眼光,沒有人在意他人的看法。舞廳就是為舞者準備的世界,只要有所求,必定有所應,一點也不復雜。來這里,唯一的事就是跳舞,舞廳外面的一切拋開,別的什么都不用管。
五首比較舒緩的舞曲過后的蹦迪,是一段休息的時間,此時舞場的氣氛達到了最高潮。舞場左側深一點的地方跳“大舞”的人也停了下來,稍做休息。“大舞就是國標,他們跳的比較專業,我們這是舞廳舞、小步舞,上不了臺面的。”一位嚼著口香糖的伯伯告訴我們。“我們來這里就是發泄下壓力。上了一天班,跳上一跳,覺得沒那么累了。不過有些單身的男女也會來這里交友,你從一個人來這里的時段、來的頻率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單身。”
據稱,這位伯伯舞齡已逾35年,對北京城的舞廳情況了如指掌。他說,挑舞伴也有玄機,講究一個情投意合,要順眼了,跳舞的時候感覺才能出來。一般女士邀請男士不會被拒絕,男士邀請女士就有可能阻礙重重。“有三樣條件:漂亮、干凈、跳的好。如果你能滿足,那么絕對是最搶手的,'',從開場跳到閉場不帶歇的。”
由于舞伴大多不固定,那么尋找舞伴、找到舞伴直到起舞的整個過程就精致起來。衣衫要整潔得體,邀請與被邀請都要有禮貌,如果跳的不好還要多加練習,其中的究竟雖學問大著,卻也純粹至極。跳舞時,人與人之間的視覺關系、空間關系和心理關系之間形成新的紐帶,隨著距離不斷縮短,個人的主體性不斷彰顯,卻又善意地為他人讓步。這就是舞者在并不寬敞的空間里跳舞,一邊能和舞伴演繹優美舒展的舞姿,一邊能不撞到到他人的緣故。卸下了日常瑣屑堆積的負擔,換上舞服舞鞋,走進黯淡燈光中的那一刻,男男女女都單純起來,仿佛回到了二十多歲的青春年華。舞蹈著的、腳步踏著的是一種情緒,而舞廳,是一只透明玻璃杯,容納了所有的恣情恣意。
我們問負責人,舞廳的經營狀況如何,他聳聳肩,說現在的青年人都不再這樣跳舞,交誼舞廳越來越少是肯定的,這一代人跳完就沒有下一代再跳,這是一種趨勢,不可逆轉。但他們并不想改變現狀。舞廳很低調,不做任何宣傳,甚至不讓我們在文中寫下它的名字,只強調介紹交誼舞的舞種和健身的意義即可,其他一筆帶過就行,他們不想改變什么。正如那不好找的入口,門開在墻上,不起眼卻存在著,舞廳見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愛恨離愁,加之于上的是歷史的卷軸,雖只是不起眼的一部分,卻也真真實實上演過那些過眼云煙。它現在悄無聲息的存在著,日后也必將如此,陪著一代人成熟,也隨著一代人離開,像燈光一盞盞關閉,最后墮入歷史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
走出舞廳的時候,回望里面的喧囂嘈雜,一位裹著玫瑰紅包裙的女士獨自走過。整場舞中,她都以一種帶著韻律的特定步伐,從站著的人背后來來回回走過。我沒來得及問她在想什么,只見她目光悠深,投向遙遙的遠處。
?讓我們一起搖擺,在此時此地
村上春樹《舞!舞!舞!》中有這樣一段:
“跳舞,”羊男說,“只要音樂在響,就盡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話?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慮為什么跳,不要考慮意義不意義,意義那玩藝兒本來就沒有的。要是考慮這個腳步勢必停下來。一旦停下來,我就再也愛莫能助了。并且連接你的線索也將全部消失,永遠消失。那一來,你就只能在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進這邊的世界。因此不能停住腳步,不管你覺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廢,務必咬緊牙關踩著舞點跳下去。跳著跳著,原先堅固的東西便會一點點疏軟開來,有的東西還沒有完全不可救藥。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為懼的。你的確很疲勞,精疲力竭,惶惶不可終日。誰都有這種時候,覺得一切都錯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腳步。”
自古以來,人的天性里就有對舞蹈的渴望,我們本質上從屬于自然,盡管是社會動物,被陳規習俗束縛也會感到厭倦。最舒服的睡姿是在大床上任意翻滾,甚至四仰八叉;最舒適的坐姿是將腳伸開,不必正襟危坐;蜷縮久了連伸個懶腰都愜意十足……舞蹈,手足的恣意伸展,是一種自由姿態的召喚。
今天,交誼舞文化已經式微,慢搖、迪廳取而代之。盡管時代和潮流的迭代不可避免,但人們對自由、對舞蹈的渴望始終不滅。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有舞。不管是過去的舞廳還是今天的迪廳,只要你在舞池里,在舞蹈著,舞步,就是唯一的現實。
---
參考資料:
《近代上海舞廳的社會功能——以20世紀30年代申報廣告為主體的分析》,胡俊修
《主宰上海灘舞廳的“彈性女郎”》,薛理勇
《當代青年文化生活的幾個特點》,宋捷
《舞曲漫議》,王淮麟
免責聲明:本文章如果文章侵權,請聯系我們處理,本站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如因作品內容、版權和其他問題請于本站聯系